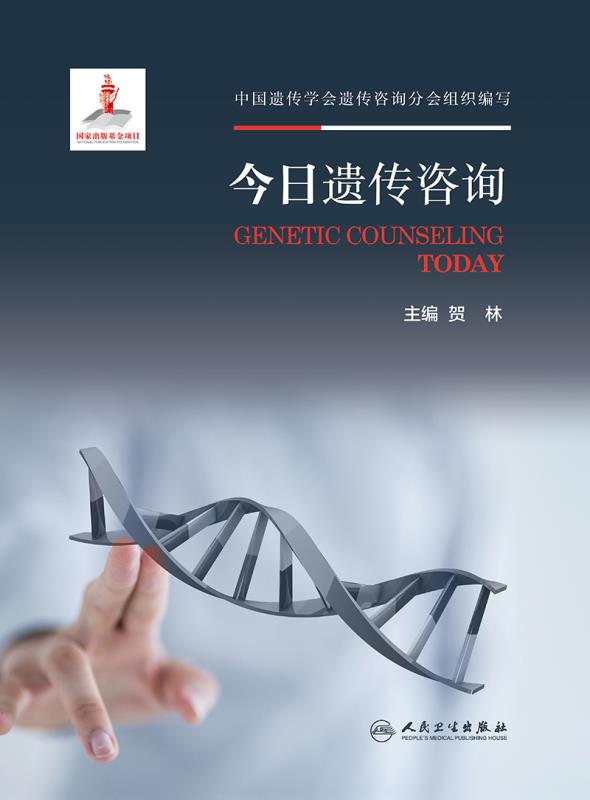贺林院士:让人们真正感知科学家的快乐

本文转载自人民政协网
贺林是遗传学界的大腕。
他和团队一起,率先完成了A-1型短指(趾)症致病基因精确定位、克隆、突变检测、验证与机理的揭示,由此揭开了遗传界百年之谜———孟德尔常染色体遗传规律也适用于人类;他还凭借成功定位“贺-赵缺陷症”的致病基因,结束了中国作为遗传资源大国,从来没有自己发现和命名遗传病的尴尬。
和文艺界的明星大腕不同,在全国两会会场,拥有全国政协委员和中国科学院院士双重身份的贺林,与同样来自上海的陈凯先院士一样,为多数人所不识。但贺林对此习以为常,拥有多少“粉丝”,并不是他所关心的事儿。
“据说,一些大众明星一场活动的出场费,可能高于一位科学家一辈子的收入。在创新驱动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今天,社会的舆论导向可能需要做出一些调整,比如引导公众去了解、尊重科学和科学家的价值。”思考了一下,贺林对记者的“追问陈凯先之问”话题做出了这样的回应。
“毕竟,一个国家的富强要靠科学和科学家。但如同生物学界的丛林法则一样,休闲娱乐也是人们的日常生活所需,只是社会舆论不应该以‘娱乐至上’作为宣传导向。”“问”答之后,贺林又补充了一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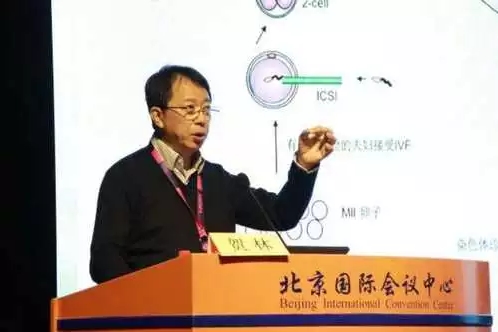
2月26日,贺林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主办的妇女健康与生育安全高峰论坛上作专题报告。
1、破解百年世界之谜
对贺林而言,生命科学领域,才是他的快乐天地。
而要讲贺林的快乐天地,家族性A-1型短指(趾)症就是绕不过去的话题。
1903年,科学家们发现,人类家族性A-1型短指(趾)症,是第一例符合孟德尔遗传规律的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这种遗传病的主要表现是患者的中间指(趾)关节缩短,甚至与远端指(趾)节融合。自此之后,该遗传病长期被作为典型案例出现在各国遗传学和生物学教科书中,世界各国科学家长期处于激烈竞争之中,希望从自己团队掌握的病例家系来找出致病基因。
“你一定听说过孟德尔遗传定律。可是你知道吗,该定律是以植物(豌豆)为研究对象得出的结论,它是否符合人类的遗传规律,却困扰了遗传学界近百年时间。”贺林用半是疑问的语气告诉记者,尽管世界各国的科学家一直在寻找A-1型短指(趾)症的致病基因,但屡屡失败,直至中国的研究成果分别发布在《美国人类遗传学杂志》和《自然遗传学》杂志上。
那是在1996年。从英国回国的贺林,以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院生命科学研究中心特聘研究组(NHGG)组长的身份,加入到寻找A-1型短指(趾)症致病基因的科学家队伍中。凭借熟知遗传学研究科学方法的优势,历经两年踩点采样,贺林团队终于在1999年找到了A-1短指(趾)畸形的2个家系,由此奠定了破解该病遗传规律的样本寻找工作。
“那2个家系共有患者47人。他们伸出双手是同样的畸形,的确比正常人手指短了几乎一节,中间指节或消失或融合在其他指节中,脚趾也是如此。”贺林告诉记者,找到样本之后,他的心情欣喜且复杂。
因为对于科学研究而言,样本是物质基础,找准样本,意味着科学突破迈出了一大步。可对于遗传病患者而言,每一个遗传病患者的出生,都是家庭和社会的不幸。
不知道是不是贺林团队的研究骨干天生具备创新“基因”,在找到样本之后的一年多时间,贺林团队又先后完成了该遗传病发病的基因定位和克隆工作。
“原来,‘A-1型短指(趾)症’的发生,是患者体内一个名叫IHH基因惹的祸———它的3个不同突变位点均能导致短指(趾)症的发生。”贺林介绍,在此发现的基础上,其团队科研人员又成功克隆了IHH基因,为诊断和治疗这类疾病带来了希望。
2001年,这项研究成果发表于当时影响因子位居世界第二的《自然遗传学》杂志。该杂志也是遗传学领域最具权威的杂志。
此举震惊了世界遗传学界,困扰科学家们的百年谜团被解开。仿佛一夜之间,贺林成为了科技“明星”。
但声名并没有带来贺林的“身价倍增”。此后,贺林依然要在单位和家之间,乘坐空间甚至不能直起腰来的双层43路公共汽车,去思考某个碱基和某对基因的命运组合。
“科学家终究和商业明星不是同一个群体,他们秉持着不同的价值观,也必然走着完全不同的路。”贺林讲话的语气一直格外平静,说到这句话时,他停顿了一下,似乎若有所思。

其实关于“A-1型短指(趾)症”研究成果的发表,还有一段插曲。
据贺林介绍,该研究成果最早投稿于《自然遗传学》杂志。但当时该杂志提出了两大苛刻选择,或是补上功能研究内容,或是再增加另一个家系。
“寻找家系的难度或许相对大些,但做功能研究起码需要10年或者8年的时间,需要制作动物模型,然后观察其对表型的影响。也就是说,仅仅发现、定位、克隆致病基因还不够,还要针对致病基因找到导致遗传病的机理和治疗对策等。”贺林表示,无奈之下,只能在寻找第3个家系下功夫。最后成功了,但的确来之不易。
至此,“A-1型短指(趾)症”的研究继续深入,这时的贺林已经开始了上海交通大学一份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同时也开始了他向《自然》杂志问鼎的部署。这意味着贺林正式把功能研究提上了日程,也成为贺林团队以及世界上同领域科学家在“新起点的共同竞争目标”。
不过,对于功能研究的赛跑,贺林团队显然比国际上的其他研究组坦然得多。因为,在研究成果发表之前,贺林团队就已经着手于功能研究了,较其他组又早了一步。
科学的一小步,可能是人类的一大步。8年之后的2009年,贺林团队完成了功能研究,成果发表于《自然》杂志,华丽丽地在世界遗传学领域为中国队勇夺桂冠。
“这首先标志着,通过基因检测、产前诊断等方式,家族性遗传病‘A-1型短指(趾)症’可以从家族或社会中被消灭掉(消灭遗传病涉及的伦理问题,这里不做讨论)。并且,该成果对于其他类型的遗传病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谈到这里,贺林眼睛里闪烁出特别的光芒。
这是一项地道的为国人长脸的工作。后来,这项研究被评选为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对此,贺林看得很淡。“奖项,只是对科学家的一种肯定形式。如果科学家把科研目标定位于获奖,那就不可能在科学之路上走得太远。”贺林笑言。
但贺林也坦陈,目前社会上的浮躁风气也影响到科学界,有些科学家逐渐偏离了研究方向和从业初心。科学家之间,也存在不少不光彩的竞争。
3、营造氛围还需媒体反思
“毋庸置疑,科学家是决定一个国家发展高度的人群。建设科技强国,也需要从尊重科学、尊崇科学家开始。但对于科学家成长和培养体系的建设,我们也需要一些‘冷思考’。”一直优雅地微笑着讲话的贺林,说到这里突然严肃起来。
在贺林看来,要成为科学家,是需要具备一定“基因”天赋的,这样才能够在研究过程中“步步快半拍”。因为科学研究不是单纯的知识积累过程,其更需要的是科学家的创造力。
“这并不是否定创新驱动过程中要加强创新人才培养,而是与其说去培养创新人才,不如说是建立良好的人才发现和评价机制,让真正适合做科学家的人可以脱颖而出。”贺林强调。
“比如说,现在我们对于科研人才的评价机制,往往是论文决定命运。论文当然是科研的重要成果之一,但更为重要的是,对于论文成果在推动社会进步中是否有实际作用?有些论文发表后,研究人员收获了诸多荣誉,但论文却难以完成成果转化,这是不是值得我们去反思?”贺林建议,在呼吁社会尊重科学、尊崇科学家的同时,科学家们以及科研的主管部门也需要去反思科研的根本目的,以及如何建立更科学的科研成果评价机制,这样才能引导科研人员在正确的道路上走得更高、更远。
贺林认为,要营造社会尊重科学和科学家的氛围,也需要媒体界反思。
“一些年轻的孩子,追‘星’是可以理解的。可媒体是国家的喉舌,媒体工作者把焦点聚集在体育明星、文化明星等层面上,是不是有违媒体人的职责?”
“科学研究是相对专业的领域,要让科学和科学家在我们国家的土壤上生根开花,还需要媒体的科普宣传。但目前,一些媒体有‘娱乐至上’的倾向,一方面忽视了对科学和科学家群体的报道;另一方面即使媒体报道出来,往往也缺乏趣味性。因而,科研被许多人认为是坐冷板凳的枯燥修行,家长们不理解科学的趣味性,也不愿意孩子们去做科研。这种状况下,我们如何去发现、去培养更多出色的科学家?”
贺林的反问,让记者有些莫名紧张。
“事实上,科研是趣味性的。你们可能很难想象,在无以计数的碱基中去寻找并定位某种遗传病的治病基因所能带给我们的快乐,那用欣喜若狂形容都不过分。”贺林边说话边打开手机,向记者展示了一张图片,那是贺林在宣纸写下的八个毛笔字——“快乐科学,感悟天地”,意思说只有快乐才有可能做好科学;只有把人看作地,人以外都看作天,才能明白人本身。
后来这幅字被学生们裱了起来,作为工作铭言。

“很多人都以为科研是一个索然无味的煎熬过程,可或许你们并没有真正感知科学家们的快乐。”喃喃自语一样,贺林结束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4、记者手记:
当科研升华为习惯……
“您是我所敬仰的科学家!”
这是3月3日记者采访院士贺林时,说出的第一句话。他先是稍微有点意外,然后腼腆地笑了,一边摆手一边说“不用,不用”。
那天,贺林戴着一副无框眼镜,身着深灰色的平纹圆领毛衣,下身搭配了一条牛仔裤,看起来休闲随性但文艺范儿十足。有那么一瞬间,我甚至产生错觉——这不是科学界的明星,而是文艺界的大腕。
不过,我也有点小庆幸他并非来自文艺界。不然,在酒店大堂,他必然会遭遇各种围堵。而我,也几乎没有可能用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听他讲述他的“快乐科学”,比如《动物世界》。但当他听我提到现代的追星族时,深感匪夷所思。
“小时候你肯定看过《动物世界》,现在还看么?我依然爱看。你们小时候爱看这个节目,可能因为没有见过那么多动物,觉得新奇有趣,或者因为它们的长相比较可爱。我喜欢看《动物世界》,是因为它们时时启发我的思考,这更有趣。”在贺林看来,很多的科学研究其实都是“好玩的事儿”。正如贺林书写的“快乐科学,感悟天地”8个毛笔字一样,他认识人与自然的角度是全新的。
什么力和怎样的季节决定鸟儿的迁徙?它们如何决定往哪儿迁?怎么编排迁徙的路线?还有鱼呢,龟呢?怎样精准地横渡大洋产卵或捕食?为什么它们具有的GPS的功能能超越电子的?又为什么许多动物能比人类更早感知地震……在贺林的眼里,这些都不是一个简单的自然现象,而是动物通过生命和自然界进行的一场场对话。
解读生命与自然的对话密码,的确应该是科学家的事。
“虽然是解读密码,却并非深不可测。就像你们要将脑海中积累的经验写成稿件一样,科学家也不过是用自己的方式将知识积累转化。只是,这个转化过程可能比较漫长和复杂。”感觉自己似乎又把科学说玄妙了,贺林自发地笑起来。
“因为漫长且复杂,所以一定要保持定力,要发自本心地坚守。”这是贺林送给年轻科学家的话,也是当年父亲送给贺林的话。
鲜为人知的是,贺林的父亲贺近恪先生,是中国大陆第一位获得世界林业科学院院士荣誉的人。作为一名爱国的林产化学专家,1951年贺近恪先生从澳大利亚回国参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1984年当选为世界林业科学院院士。
贺林很少在工作场合提及父亲,但深受父亲影响。如今,他也这样教育他的学生——搞科研是一个积累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研究者深入其中的坚持不懈;科学研究有时候就像探险,穿过最艰难的山重水复之地,再向前走一小步,就会柳暗花明;当科研升华为习惯或常规,科学研究就会成为一片快乐天地,研究者也才真正发现并体会到创新创造的无穷魅力。
科学如此,其他领域不同样如此么?当真正投心于某项工作,并做到极致,又怎么会不开花结果呢?所以,今天我们呼吁尊崇科技创新,也是应该从崇尚科学家精神开始的吧。(本网记者 刘喜梅)

 推荐书籍
推荐书籍